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▌杨帆
被文学史长期忽视的作家里,阿湛算得上是一位。他以其地道的绍兴方言、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普通人的忠实记录,在民国文学的长卷中,留下了独特而温润的一笔。

《晚钟》扉页
【故纸遗珠】
1935年至1948年,上海开明书店陆续出版现当代文学丛书,其中包括散文妙手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欧游杂记》,艺术大师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》《缘缘堂再笔》,亦不乏凤凰之子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,学者钱锺书的小说《人·兽·鬼》等。五十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,悉数辑入《开明文学新刊》,颇似一座现代文学聚贤楼。
丛书中,多为名家之作。普通人之于大家,犹如登高者攀登,多是欣赏斐然之文笔,感悟高山仰止之风范。在名家林立的文学殿堂里,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——阿湛所写的《栖凫村》提供了更接地气的视角,引起我的兴趣。阿湛,本名王湛贤,浙江绍兴人。栖凫村,位于绍兴越城区,是清末藏书家徐树兰的故里。
今年春天,我偶得这本轻巧的小书,一经翻阅,为之触动。随后,我陆续购入阿湛的另外两部短篇小说集《晚钟》《远近》,细细品读,窥见家乡的光阴流变,只叹相遇恨晚。这位绍兴同乡颇有讲故事的天赋,如乌篷船头的老客,用一口乡音,娓娓道出一星半点的旧事残影,随那水乡的溪流,一道淌进人们的心田。
《栖凫村》出版于1948年3月,共收入8则短篇小说。尽管有关阿湛的生平资料寥寥,但四十年代的这一节点,足以想见他的遭遇。抗战胜利前夕,他跟随柯灵先生,在上海担任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《中央日报·文综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。他与家乡绍兴之间,不仅隔着一堵堵空间上的墙,更因战火炮声,与往事隔了一层时间的纱。然而,家乡总归是家乡,一提到故乡故景,笔下仿佛生出光芒。
“埠船穿过市梢的洞桥,船底掠着冒出水面的渔塘的竹笆,在令人牙痒的‘刺刺’声中,摇近村庄来了。
船夫当中的一个放下橹,敲起那面小锣来:
镗镗镗,镗镗镗!
这是永远年轻,永远快乐,彷佛响亮的欢笑声似的锣声,我几乎想象不出那个矗立在船梢上,从自己的手里敲出这愉快声音的人该有多幸福!”
这是《船夫》的开篇。洞桥、鱼塘、村庄,随一位摇橹敲锣的船夫出现了。读者仿佛坐在乌篷船上,逐渐看到埠船船夫“头脑”与赵六叔的日常生活。他们摇船往返于各村,接送乘客、传递货物。这则小说极短,几乎没有情节,但传递了阿湛创作的理念:“这些最最真实而平凡的人物,他们的一生几乎是没有故事,没有开头和结尾的。为人们劳作了一生,辛苦了一生,最后是衰老和死亡,很快地从人们的记忆里失去。”他为普通人创作,写普通人的生活。普通人的生活虽是日复一日,古井无波,但抱有自己的信念。“纵然有外力磨折了他,但始终不能摇动他对于求生的钢铁般的坚信。人是为了活着才吃苦,并不是为着吃苦才活着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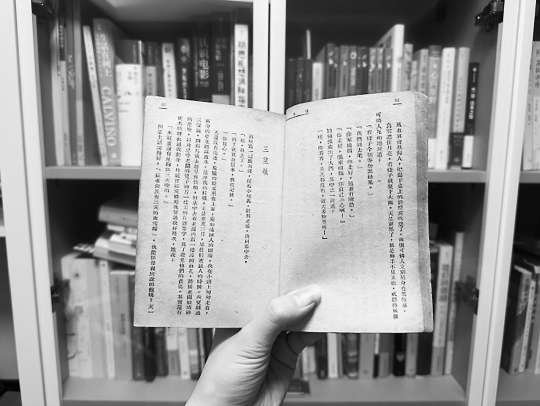
笔者购入的《栖凫村》内页图
【乡音如诉】
方言,是一方水土的人文密码。金宇澄用沪语写就《繁花》,利落短句如刀,剖出黄河路的旧事。韩少功在《马桥词典》中,以词条为经纬,重构方言中的乡土村庄。而在《栖凫村》与《晚钟》中,阿湛以细腻沉静的笔触,将绍兴方言融入叙事肌理,使小说升华为一方水土的文化表达。读他的文字,仿佛穿墙掀纱,听到一个个普通人,在命运的戏台上,开口唱起各自的戏文。
阿湛对方言的纯熟运用,最动人之处在于那种高度的生活化与地域真实感。“赖学”(逃学)生动勾勒出学童的顽皮神态——“学校里读书你眼热?”“我不眼热。我只觉得有书读是福气。”“眼热”一词,意同羡慕,道尽最质朴的渴望与比较。这些语言,仿佛是活生生的、带着体温的日常。“三兄弟也勿好算多,等你成了亲之后,我把你们分开,让你们各管各好好的做人家。到今朝为止,五姊妹当中就剩你一个人还没有做事体。”其中“做人家”(勤俭持家)三个字,则凝聚了绍兴人代代相传的治家智慧与生存哲学。《为了分家的缘故》写了一场家庭闹剧。大媳妇为逼迫婆婆分家,假装被鬼附身,闹得全家鸡犬不宁。婆婆最终同意分家,大媳妇的“病”也奇迹般痊愈。人性中的自私、算计,透过“做人家”这面多棱镜,折射出别样的亲情张力。
在描绘生存困境时,阿湛的方言书写则显露出其沉郁的底色。《三望岭》便是极好的例子。故事简单而沉重:天未亮透,“我”为生计所迫离家回城,途中遇见同样贫苦的阿宝母子。“我”的母亲心疼挽留:“米缸里还有足够你三天吃的。”一个简单的倒装句——“足够你三天吃的”,而非“足够你吃三天的”——将母亲希望孩子多留三天的不舍,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而阿宝母亲的倾诉更是朴素得令人心酸:“店里做做总好的,事体也轻便。我也想给阿宝去学生意,祇是没有人荐。捐款捐米这么重,保甲长日夜上门来催,我们自己只好吃‘胡涂’了。再不给阿宝出门去,要把他搭浆死了。”“胡涂”指的是浆糊、糠粃混煮的贫民食物,“搭浆死了”意为困顿潦倒至死。
在这些母亲的口白中,阿湛并未堆砌土语,而是择其精要,将方言融入人物的口吻与命运的底色中,使不懂绍兴话的读者也能心领神会。这种文学化的处理,让方言不再是文本的装饰,而是故事的呼吸、人物的骨血,是回响在字里行间的“晚钟”,深沉地叩击着关于乡土、命运的永恒命题。
绍兴人爱听戏。我幼时常随外婆听绍兴“莲花落”,在村里的稻地上,看戏班搭台唱戏。锣鼓声与戏曲声,总伴随着节日的喧腾。而阿湛的耳朵是灵的,他能听出那浮华唱腔背后,普通人细微的抽泣与叹息。“官人好比天上呀月,为妻的好比月边啦星……”《神仙拐子及其他》一篇,便从这样一个唱戏的夏夜开场。乡长一家与村民聚于“大道地”。乡长的儿女唱戏,胡琴咿呀,唱词婉转,村民闲聊。佃户阿兔不过想续种那块名为“大五亩”的田地,却与乡长发生冲突。老实巴交的他,被乡长出口辱骂,被扇巴掌,“鼻孔里流下来黑曲曲的两条,像蚯蚓”。乡长是地方官,看似芝麻点大的位置,于乡民而言,则是大权在握。村民同情阿兔,但无人敢言。不多时,“人散,声寂,夜凉”。那座巍峨大宅里,胡琴声再次响起,只听得戏文依旧唱着:“官人若有千斤担,为妻的分挑五百斤。”戏里的情深义重,与戏外的冷酷压迫,在此刻形成无声而残酷的对照。普通人沉默的苦难,也随着这夜曲,继续了下去。
【水岸悲欢】
曾任《文汇报》编辑的张香还,在2018年写下《点滴忆阿湛》,追忆往昔。抗战胜利后,他到上海出版公司拜会柯灵,恰遇阿湛。“在这个地处闹市临马路的小小编辑室,暗弱的光线中,柯灵先生和唐弢先生写字桌的一边,坐着一个埋头于笔墨的、脸庞白皙的瘦瘦的年轻人。看上去他才不过22岁光景。柯灵先生为我们作了介绍,这就是阿湛。”这个埋首案头的年轻人,经历战乱,目睹诸多无常之事,这些都深深印刻在他的作品里。
《钓醉虾》便极有时代特色。“县督学……已经……到……我们……学堂……话勿来……就要到……”开篇,一个学生急促的呼喊,瞬间打破午后的宁静。保国民学校即将迎来县督学的视察,两位驻校先生顿时手忙脚乱——原来校长是关系户,年仅二十出头,为缓服兵役、领份薪水而在学堂挂职,却从不露面。更荒诞的是,学校名册上明明写着“教员五位,学生近百”,实则仅有教员两位、学生二十余人。面对如此窘境,校长与教员竟想出了“借”私塾学生充数、让不识字的乡长女儿冒充教员的荒唐对策。三人又借酒桌周旋,请督学喝酒、谈天、干杯,又猜拳,又喝酒,直灌得督学在乡长家酩酊大醉、鼻血横流。此法奏效,学校最终获得好评。这一切都被私塾先生冷眼旁观,“他是冷笑:笑那一席丰筵和一坛状元红的力量”。视角的悄然转换,不动声色地揭穿了这场闹剧的虚伪,也映照出乡村权力运作的真相。
阿湛不仅写乱世中的荒诞,更着墨于命运无常对人心无声的磨损。《晚钟》整部集子,都在书写身边人不可预测的遭际,且总伴随着极具象征意味的景物。
在多数人眼中,彩虹是幸运的象征。小说《彩虹》中,“我”被长工四六接去参加好友卢凯先的婚礼,途中偶遇一道绚烂的彩虹:
“彩虹使我想起一个念头,祝贺我的好友新婚幸福;我从四六的眼睛里看得出,他同样也有一个念头:祝贺我的小主人新婚幸福。我们两个人的思想,在这河面上,彩虹下,晚风里,静穆中,似乎正藉着某种力量在相互吸引,终于在祝贺卢凯先新婚幸福这一点上碰了头。碰头之后,两个思想立刻就分手,各为自己编织未来的美梦去了。
不幸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短暂的,彩虹渐渐褪色,转眼就已经不见。”
这一笔转折,恰似命运的岔路口。婚礼当天,四六为挂灯不慎摔伤,最终成为跛子。一年后,“我”再访卢家,得知卢凯先已在婚后不久中暑身亡,其妻成寡,双目昏沉,“头上别了一朵白色小花,仿佛雏菊大小”。彩虹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强烈反差。在天灾人祸到来之前,一切稀松寻常,毫无征兆。究竟是谁在翻云覆雨?眼前又是一弯彩虹,神似一年之前。阿湛在文末留下无声的叩问:“对这古怪人生,我不知作何解释。”
有时,阿湛笔下的自然景观与人物的心理深度交融。《苦竹溪》中缪伯祥在苦竹溪溺水身亡,同学们打捞其遗体未果,最终发现他溺死溪底。在阿湛笔下,月亮极冷,泛着淡青色,叫人想起月光下的苦竹溪。
“我空着两手走在大埂上。这大埂离苦竹溪有好几百里路。好几百里路,多远。我的两肩空着。是的,一点东西也不负荷,这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。但是我觉得很重。整条苦竹溪,全压在我的身上了,从两肩直到胸口。”
故事通过“我”夜访缪家,展现其父母对儿子生死的无尽追问与绝望。其母叩头念经,问不出儿子的未来。其父背手踱步,欲说还休。苦竹溪的冷月、溪水,暗示生命如流水易逝,人也如鱼与棉花般脆弱。
这字里行间的无常之感,既是时代底色的映照,也暗合了阿湛自身的命运。据张香还、马国平回忆,阿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《新民报》文艺记者、《儿童文学》周刊编辑,后来病死在青海的农场里。读至此处,小说里那阵阵晚钟声,仿佛又一次在耳畔响起,余音苍凉。
时光流转,乌篷船的橹声渐远,栖凫村也已换了模样。然而阿湛的文字,却让一片土地的温度、一群普通人的悲欢,在纸间获得不朽。重读阿湛,是为了在众声喧哗中,听见那些始终沉默的大多数。《栖凫村》是一部用绍兴方言写就的“平凡传”,而那回荡在书页里的晚钟,既为逝去的时代送行,也在提醒着我们:文学最本真的力量,永远来自对普通人命运的真挚关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