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■ 杨早
本世纪初,洪子诚老师在北大上《问题与方法》课,我坐在第一排。课中洪老师提到“潮汕人普通话不好”(洪老师是广东揭阳人),本是自况。看了我一眼,洪老师又说:“陈平原例外。”满堂哄然。
说这件往事,是感慨于洪老师有观察入微的能力,又有举重若轻的精神(若笔者不是师从陈平原老师,大概也不会有这场笑谈)。那年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首发,在北大中文系座谈,赵园老师有“老吏断狱”的评语,至今不能忘,亦当以此观洪子诚老师诸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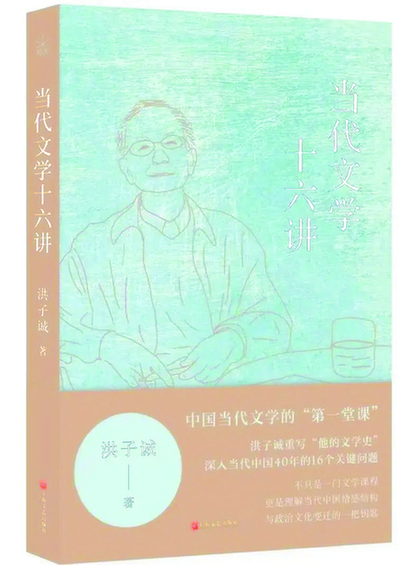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洪子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是讲稿,但洪老师之作,一向有讲稿胜于专著的美名,如不止一人讲过,中国香港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胜于后来用作全国大学教材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,盖讲稿更便于讲者自由发挥,更利于单刀直入问题。简单说,是讲稿更见出讲者性情,不用顾忌方方面面,更能见出讲者功力。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从1949年论及上世纪80年代,正是洪子诚老师用力最深的阶段,也是他亲身亲历的阶段。换句话说,个人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步。更妙的是,洪老师一直在高校读书、教书,是个所谓的“臭知识分子”,不曾身列工、农、兵行列,这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知识特区和信息茧房的干扰,给了他更好的观察文学史的角度。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并不是从空白开始讨论“当代文学”,我想读此书者,有三个前提是必须了然于心的,否则读不通本书。这些前提如:
(一)当代文学与政治形势密不可分,当代文学中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问题,还包括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;
(二)当代文学进程中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;
(三)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,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独立于世界文学发展。
这跟一般人想象中的“当代文学”是不一样的,但更贴近历史的真实。作者在第一讲里便讨论《疑窦丛生的“当代文学”》,提出了“现代文学”替代“新文学”,是为“当代文学”的生成给出空间。或者说,“当代文学”创造了“现代文学”。这个说法比较拗口,却反映了作者的洞见:“新文学”是一种性质的界定,而“现代文学”则兼性质和时段而有之。而“当代文学”明确了现代文学的下限,也将“现代文学”的性质标示了出来。由此作者总结为:
194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也可以看作“国家文学”,是由国家统一对文学生产全过程进行管理的文学,包括成立全国性的作家组织,国家管理文学出版、流通传播过程,制定统一的文学方针政策,对创作的政治艺术做出鉴定、评价。(P12)
这个定义里实际包括了笔者上述三点前提,但揭示更为明显、精练,也很好地阐释了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提出的“一体化”概念。事实上,这是统摄全书的观念,后面的阐述,要在“当代文学即国家文学”的基础上加以理解,否则就得不出可靠的结论。
紧接着,作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《当代文学的“地形图”》,这其中既包括国统区偏“自由主义”作家的隐退,晋、陕等解放区作家群的崛起,也包括上海作为“文学中心”的文化衰落与北京的独大。这一文学地理的变化,“从东南沿海向中原、西北的转移,体现在取材、人物、风格、语言等多个方面”,“作品从比较重视学识、才情、文人传统、日常生活、风土习俗,到更重视政治意识、社会政治运动、各个时期的政策,从更多表现市民、知识分子到更重视表现身为‘人民’主体的工农的生活和斗争”。(P32)限于篇幅,作者没有过多分析单篇作品,但是熟稔当代文学作品的人都知道,作者的概括是准确的,也是合乎逻辑的,它跟整个国家步入“新时代”有关,也奠定了当代文学的基调。
接下来,作者按照顺序,抛出了当代文学中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。这些问题中,有些是当代文学界争议已久的,如第五讲《“组织部”里的文学成规》、第六讲《“人民大作家”或“乡村治理者”》,有些是作者不止一次在论著里讲到的,如第十二讲《新诗潮:寻找新的符号系统》、第十三讲《拒绝的诗歌美学》,将作者擅长的当代诗歌史研究融合其中。而另一些,是此前任何一本当代文学史论著都不曾提及的,属于近年作者的独到见解,其特点是: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放在世界文学的潮流中去考察,关注文类之间的升降及其原因,将政治动因融入文学事件之中。如第三讲《“苏联化”与“去苏联化”》、第四讲《中篇小说的“发明”》、第七讲《历史提的问题,回答得了么?》、第八讲《19世纪文学:“怀旧的形式”》、第九讲《60年代的“戏剧中心”》,等等。有些是旧话,作者也明说吸取了其他学者的观点,但放在全书中,却自有一种“史”的妥帖,如第十讲《当代文人的另类写作》、第十四讲《“卑微者”的小片天空》、第十五讲《文学里的城市空间》。
对于写史最敏感的分期问题,作者用第十一讲《延长线上的“新时期”》就解决了,并精辟地指出:“80年代文学,既是变革、转折,同时也是当代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延伸。”这一延续性,过去是认识不足的,现在提出来,是因为“一、当代文学基本制度、观念、艺术方法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,而是在有所调整的基础上的延续;二、在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冲突的各种文学主张、创作倾向,到了80年代地位发生了‘结构性’的变化,某些曾被压制、批判的论题被重新提出和肯定,如‘写真实’‘干预生活’,如对‘现代派文学’的看法”(P180)。作者认为,这样做,并不是要否定80年代的重大文学变革,而且要注意“新时期”与此前文学的对话关系。不同的历史时期,强调“变”或“不变”,因应的是不同的史述主流和历史认知——曾有研究生告诉我,他们最难理解的不是“十七年文学”,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,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代文学的本质和对话关系认识不清。新世纪以来,笔者提出的“重新发明文学”也可能看作一种“断裂”的宣言。对于文学发展来说,宣言“断裂”或许是必要的,但对于文学史而言,强调“连续”才能看清历史的传承与吊诡,理解其中的逻辑。
从体量来说,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是一本小书,也不承担分析作品、解读作家生平等耗费大量篇幅的任务。但是从提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而言,这又是一本大书。作者秉持一贯的态度,知人论世往往不下断语,而是以疑问句出之,留下后面无比广阔的空间。读完此书,对于“什么是当代文学”当有一个充分的认知,这种结构性的认知才是引导我们读史求智的有用津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