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徐 风
我年少时生活在一个江南古镇,外公是陶器店老职工。他经常要在店里守夜,寒冷的冬晚,我经常去陪他焐脚头。那是在陶器店的阁楼上,一张简陋床铺的四周,堆满了各种陶器——大到缸瓮盆钵,小到碗碟壶罐。我最早的器物启蒙,就在这阁楼上。
外公的店铺连接着百姓的烟火生活,每天一早,顶着晨露上街的农人们挤满了柜台。从猪槽鸭盆到碗碟瓢盏乃至祭祖的香炉、船家的行灶、腌菜的陶瓮、煲汤的砂锅、煎药的陶罐……五光十色,声响铿锵,编织成一幅幅温煦的百姓生活图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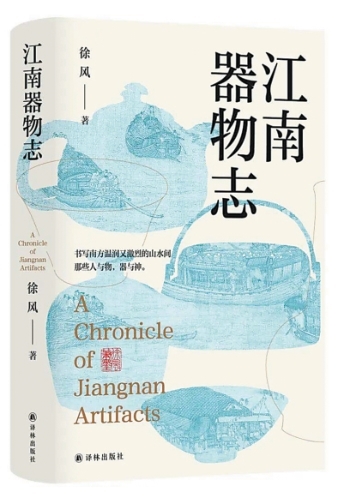
《江南器物志》:徐风著;译林出版社出版。
我的器物文学书写始于紫砂壶。一把茶壶的背后,连接着江南的手艺史、生活史、审美史。因此,我注重壶与人的精神相依,通过书写壶中乾坤,来传递人世间的暖意与江南文化的气质。后来我发觉,紫砂壶远不足以承载江南文化,进而希望通过对一个地域烟火生活的百年书写,让陶器、木器、玉器、漆器、酒器、农具、文玩、杂件等“器物群”在生活中以活色生香的形式呈现。一个小小的野心,起始于用文字搭建、还原一座烟火漫卷的江南古镇,以呈现它气象万千的日常肌理,于是就有了《江南器物志》的书写。
器物作为人们无声的陪伴,储存过往又经历现在,在岁月的流淌中,也有了自己的灵光。或是睹物思人的念想,或是见证天地的信物,因为有了故事,很多沉睡的器物,从时光的皱褶里走出来。
车水巷的人们离不开郑龙大,每年夏天,连续不下雨的时候,稻田里开始龟裂,如何把河里的水引到田里?郑龙大的龙骨水车便威风凛凛地上阵了。这位熟谙农事又精通农具制作的老农寿星活到了99岁,他的去世,成了镇上的一件大事,因为他的高寿,也因为他的手艺出众。高寿老人去世,其家族会邀请前来送别的人们吃豆腐饭,用来盛饭的碗被称为“发碗”,只是郑家这样的农户用的是一种极便宜的繁昌碗——碗大,拉坯粗瓷,紫茄釉,耐脏。比不得大人巷里那些退隐而年迈的耆宿所用的诸葛碗,也比不得车水巷里少许亦农亦商的殷实户头用的敦式碗,但那天,器隐镇上的人们无论贫富,都想得到一只郑龙大的“发碗”——人们在乎它的稳重敦厚,在乎碗底那个“寿”字。
郑龙大在器隐镇上,更在我的记忆深处。他是那些每天来陶器店里挑选日常用品的父老乡亲,是某件器物上所留存的生活印记,抑或是潜藏于生活方式中的文化基因……有形的器、无形的气交融在一起,如竹器“宁折不屈”的气节、医器“阴阳平衡”的美学,在器物中识得江南,不仅是形,更是神。科举、稼穑、风俗、舟车、食谱、药方、字画等这些俗世的日常在书中交替呈现。由此派生出官吏、书生、师爷、农人、商贾、郎中、艺人、民妇、工匠、讼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,他们各谋其所、各求其好,在“器隐镇”这个道场上,以各自的阅历,述说着他们的过往人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