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作者:解玺璋
最近读了作家京梅的《八九雁来:姥姥的聊斋》。这本书体量不大,开本类似当下流行的口袋书,读起来却让人不忍释手,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,将自己一生的故事同外孙女娓娓道来,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常有的事,生活中并不多见。
读这本书时,我常常想起我的奶奶,她抱大了我们兄妹五人,在我十八岁那年,她去世了。那是我当上工人的第二年,还来不及更多地孝敬她老人家。但是她对我的好,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对她的思念中。在这一点上,我很羡慕京梅,时间给了她机会和能力,可以把姥姥的故事娓娓而谈记录下来,著述出版,使她与姥姥的善缘得以功德圆满。而当年的我,是不具备相应的机会和能力的,奶奶也只能带着一肚子的故事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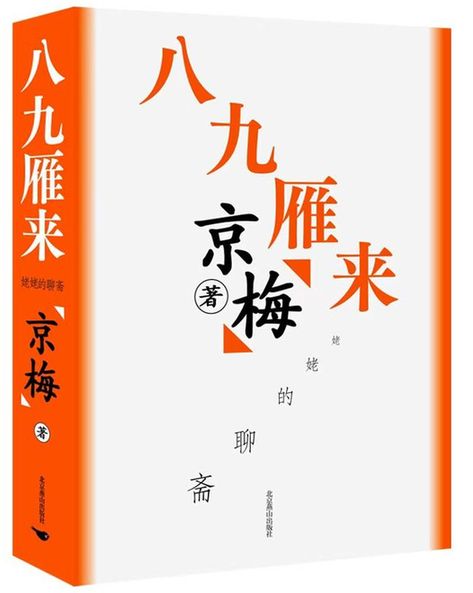
《八九雁来——姥姥的聊斋》京梅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5年8月第1版
我的这点自怨自艾本不足论,而只是想回应京梅在“缘起”中提到的一点想法,即将“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”的故事记录下来,从而提供一种与“当代文人传说中美好的民国时代”不同的认知。这是一种不错的想法,恰好应和了当下历史写作从微观到个人化的潮流。写帝王将相的固然很多,却也有写宫女、小吏和兵士的。现当代作品也常有所见,较早的就有“北漂诗篇”,陆续便有了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写作中来,他们中有一线工人、外卖骑手、公司职员、保洁女子和田间农民,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老人。这些带有个人化叙事特点的作品,多采取自述非虚构的方式,表现的都是个人生命历程,并由此折射出社会变迁和时代色彩。京梅这部《八九雁来:姥姥的聊斋》所述聚焦于民国至新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,和许多人所热衷的名士淑媛、名门望族的生活场景不同,姥姥所提供的主要为“穷出来的知识”和穷苦人的生活场景,从而弥补了以往历史叙事的不足。
叙事方式上,京梅采取了姥姥口述,并由她整理、订证、辨析的做法。姥姥的身世并不复杂,她的娘家在德胜门外真武庙一带,住在那里的多为厨子、轿夫、做小买卖的,都靠手艺或卖苦力为生,经济上稍好一点的,就不住这儿了。姥姥的父亲就是个厨子。姥姥五岁时死了娘,她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。母亲没了,全家人的生活就由父亲一人承担。那时办红白喜事,讲究搭棚请客,父亲有时接了为人家做席的活,常带两个哥哥做帮手,家里就剩下五六岁的小女儿。这里没有让当下北京人自豪的四合院,院里只有南房三间,北房三间,住四户人家,姥姥家住两间北屋。晚上害怕,怕人也怕鬼,嗓子眼儿里跟堵个大疙瘩似的……
姥姥的故事就从娘家讲起。她的叙述平静而安详,绝非是很多年前我们听忆苦报告那种满腔仇恨控诉的口气。姥姥固然是个苦命人儿,十岁多就跟着姐姐进厂做工去了,十二三岁给毛纺厂做加工,纺毛线,有时也择羊毛,一天挣六个大子儿,够吃棒子面的。但姥姥也是个聪明人,记忆力超强,八九十岁的老人说起儿时民谣,朗朗上口。比如:“初二、十六,毛厂的吃肉,每人四两,七折八扣,掌柜的盛一碗,不管伙计够不够。”还有:“一根拐棍儿我拄着;两撇胡子我捋着;三炮台我抽着;四轮马车我坐着;五(武)家坡我听着;六国饭店我吃着;七层高楼我住着;八圈牌我打着;九块钱我掖着;十(实)在不成我走着。”她说,这都是那些穷人,看富人过好日子,心里羡慕,只能编个歌谣过过嘴瘾。
从姥姥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很多穷人过日子的场景。比如讲到去观音寺打粥,可谓细致入微,打粥人如何,舍粥人如何,说得清清楚楚;最让人感动的,是打粥时天寒地冻,排队时间长,手脚都冻僵了,“为了我打粥,你太姥爷还给我做了一个棉手揣子”,看出父亲对小女儿的细心呵护。后面说到雍和宫腊八舍粥,就相当隆重了:“每至腊月初一日,总管内务府派官员率苏拉至府库将各类熬粥食材、家什、柴禾等备齐,初二开始运往雍和宫,初五运齐。初六,皇上派蒙古王公一人,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,率内务府三品以上官员、厨师、苏拉人等,至雍和宫监督称粮、搬柴i。初七早晨,蒙古王公择吉时下令:小喇嘛生火;经验丰富的喇嘛掌勺熬粥,依次将奶油、小米、江米、红枣、核桃、桂圆、瓜子、葡萄干等放入锅中。初八丑正(凌晨两点),第一锅粥熬熟,即以碗盛供奉佛前。蒙古王公进宫复命;全体僧人开始在法轮殿诵经,百盏酥油照法轮通明,香烟鼓乐昭释门庄严;清晨,雍和宫喇嘛向京城百姓舍粥。” 这风俗延续至今,只是不再这么繁琐了。穷人家就不能太讲究了,有什么搁什么,煮点小米儿、芸豆,搁几个花生,那也算不错了,还有喝不上的呢,只能上庙门口排队等着舍粥去。
姥姥所讲述的“穷出来的知识”,我们这一辈有些是经历过,或见识过的,更年轻的就未必了。比如她说的“打胳膊”,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这种生活经验,我却并不陌生。当年我妈给几个孩子做鞋,都是先打胳膊,剪成鞋底儿的样子,再用麻绳纳鞋底。还有她说的“请会”,后来叫“互助费”,现在恐怕也没有了,当年却是相当普遍的,几乎每个单位的工会都有义务帮助职工组织和管理这件事,并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度过难关。像这样的事,如果不是姥姥这样的老人讲出来,不仅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会提及,而且,清高的文人叙事也是不屑一顾的。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和独特价值所在;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言,历史记述者“所应负之责任也”。
书中还安排姥姥依次讲述了二月二龙抬头、三月三蟠桃宫、清明节、四月一的“头道茶棚”、五月初五端午节、七月七女儿节、七月十五中元节、八月十五中秋节、九月初九重阳节、十月一,鬼穿衣、冬至、腊八、腊月二十三小年、年三十、大年初一、初二、破五、正月十五元宵节、雍和宫打鬼(正月二十九或三十)等,这一年中所有年节的讲究、规矩,都讲得生动有趣,读后大开眼界,有些内容是可以弥补民俗史叙事之不足的。比如讲“头道茶棚”,我们听说过当年有去京西妙峰山娘娘庙进香的习俗,但是,从未听说过沿途还有十几道茶棚,而且头道茶棚就设在德胜门外,从四月初一早晨就有人烧香,一直延续到十五,大伙儿都烧香,还有拜香的,打远处磕着头来的,由这儿出发,上妙峰山拜娘娘。除了进山烧香的,还有卖吃的的、舞狮子的、耍幡儿的、耍叉的、耍棍的、敲锣打鼓的,那种热闹,是今日那些所谓庙会、大集无法比的。
此处不宜过多地“剧透”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书来看。而我不能不称赞此书的,是京梅整理、编校此书的态度,非常严肃认真,绝不敷衍了事,这体现在她为了考订姥姥所述之真伪,追溯历史真相,不仅翻阅了大量的明清、民国的文献和笔记,甚至做了一些必要的田野调查,并写下了几万字的考订文字。近年来,口述史相当流行。很多人或不了解做口述史应有的学术标准,或不肯下大功夫,贡献出来的往往是口述者的“原生态”,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。借用傅斯年先生的说法,史料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,那么,口述则类似于直接史料。直接史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,应是比较可信的。但直接史料也有自己的短处,即或为孤证,或因时间久远,不能保证记忆准确,或因各种难言之隐,未能将真相和盘托出。因此,很多时候,直接史料还需间接史料的佐证和补充。间接史料虽不如直接史料更靠得住,但有些间接史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史料所得,也是不该轻视的。京梅就很善于利用间接史料与姥姥的自述互相印证,增强了口述的可信度。比如她对姥爷家祖坟和族谱的追寻,大可看出她的执着和用心。我还记得她在新疆伊犁参观将军府旧址时的专注,当时不知她的用意,读了她在这本书中所写“作者按语”,才真正明白她的用心之良苦。她这一长篇按语,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篇关于家族史的论文。
最后还应提及的,是百岁老人李滨声老为此书绘制的数十幅精美插图,一如他的传统风格,简洁、生动、有趣而幽默,给阅读此书的读者增添了许多乐趣。而书中的老照片,不仅丰富了该书的历史感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姥姥的慈祥、善良,也更理解了京梅对从小抚育她长大的姥姥的感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