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吴 真
兵火世难,书籍在劫难逃。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,中国计有3744家图书馆,至1937年底,损失达2166家之多,损失图书接近9000万册。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的官方数据,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灭顶之灾,其损失之巨,至今无法统计。
1937年8月13日,淞沪会战爆发,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:走,还是不走?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,而且他分藏于上海各处的古籍有近2万册。最终,他选择留下。由此有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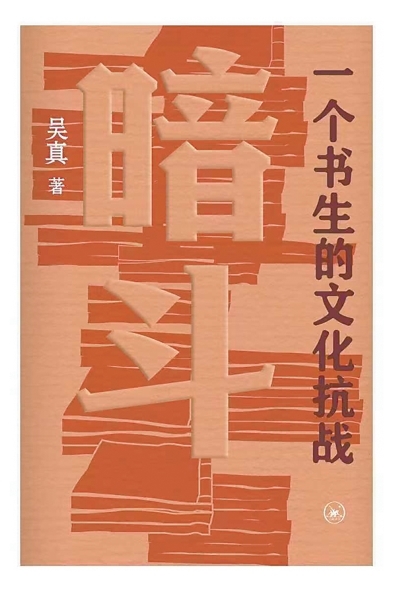
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:吴真著;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在上海“孤岛”的前4年,郑振铎耗心力于搜罗访求文献,与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的诸同仁抢救下1.5万余种宋元善本、明清精椠;后4年,他隐姓埋名,典衣节食,尽力于保全、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。
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隐秘行动,每一个师团均配备“兵要地志资料班”,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,拟出“接收”(没收)清单,一俟占领,立即展开掠夺。在日军劫掠之后,大量的劫余古籍流散至上海,由于战局动荡不安,贪腐盛行,书画、古籍、古董作为“硬通货”也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储财、生财的主要选择,旧书业因此畸形繁荣。
虽然名义上是为国家保存文化,但在国家力量暂时缺席的上海租界,郑振铎的文献抢救工作,只能遵循古旧书业的商业规则,以个人名义进行秘密交易,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。每一次出手,都是非常时期斗智斗勇的博弈求生。他始终处于被“围猎”的危险境地,其行动,其研究,其藏书,一直受到日本军界、情报界、学术界的密切注目。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,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,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”,又一次次地“从劫灰里救全了它,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”。
这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,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谍战,归根结底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保卫战。
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一书讲述的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暗战,讲述郑振铎在险恶环境中,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中,在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,抢救保全文物古籍的故事。通过解读日方、汪伪的档案,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、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录,我们得以走近这场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。
烧书以逃死,售书以求生,抢救书籍以抗日,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。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,也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,记录下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。例如,对于之前常被描绘成唯利是图的书贾群体,郑振铎说:“我很感谢他们,在这悠久的8年里,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。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,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。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伙计,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近3万册古籍,利用民间商运方式秘密运至香港,穿越军事铁幕,打通了一条隐秘的“孤岛书路”。
钱振东《书厄述要》指出:“文化之于国家,犹精神之于形骸。典籍者,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。”“书厄”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图书亡佚残缺的劫难。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触目惊心的“书厄”,郑振铎坚信:“我们的民族文献,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,这一次也不会灭失。”他生前经手搜购、抢救、保存的古籍,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。在他导夫先路的中国俗文学研究、版画研究、文物研究诸领域,今天的研究者们所研究的珍贵文献与文物,许多都是当年郑振铎奋力搜求保全下来的。
时隔将近一个世纪,回望这场“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”,回望抗战时期郑振铎艰苦卓绝的书籍事业,更能深刻体会到它之于文明传承保护的意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