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◎念一
对文学青年来说,李劼人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家。熟悉在于,他的长篇小说《死水微澜》已然是经典之作;陌生在于,许多人并没有读过李劼人的其他著作,在阅读普及上,他明显不如张爱玲、沈从文等同期名家出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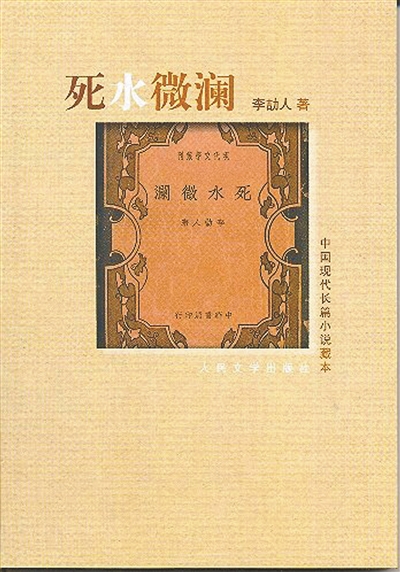
仍被低估的“大河三部曲”
我第一次读李劼人是在本科期间。但那时囫囵吞枣,不得要领。真正痴迷于李劼人的语言,一头扎进他的文学世界,已经是上班后的事情。在我的记忆里,读《死水微澜》的感受近似于《金瓶梅》。这本书可以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去解读,可如果停步于此,或许会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聱牙诘屈的小说。《死水微澜》更像一部活色生香的社会万花筒式电影。它的叙事节奏很灵,似豆子在油锅上翻滚。它酣畅淋漓地呈现欲望,不寓褒贬,学术上说它是自然主义,其实它接续的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传统。哥老会、邓幺姑、袍哥,各色人物在小说中渐次登场。民间信仰、伦理冲突、四川民俗,李劼人写出了现代成都暴风骤雨又坐怀不乱的浮世烟火气。在1935年6月14日写给舒新城的信中,他曾说:“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。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。”《死水微澜》是民国时期第一流的世情小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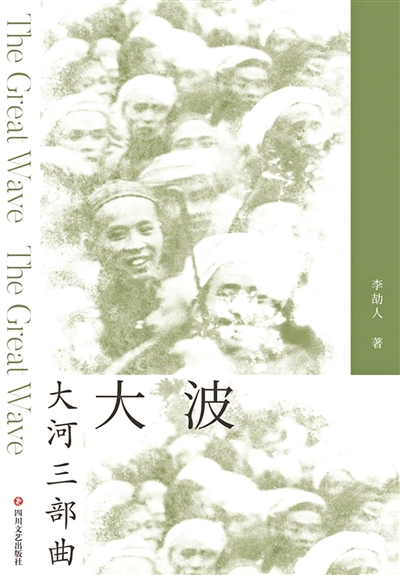
接着《死水微澜》,我继续看了《暴风雨前》和《大波》。《死水微澜》的时代为1894年到1901年,《暴风雨前》的时代为1901年到1909年,《大波》是专写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,三本书合为“大河三部曲”,这也是李劼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本书。
跟《大波》的体量比起来,《暴风雨前》是一本小书,这本书写出了清朝末年社会的动荡,对官绅子弟、袍哥、进步知识分子和乱世中的女人群像描绘得很形象。书中写女犯人被活剐,令我想到莫言的《檀香刑》,考虑到可能引起读者生理不适,在此不贴出原文。
《大波》在优缺点上都极为突出。它在结构上不如《死水微澜》精炼,李劼人讲保路运动,洋洋洒洒80万字,像是编排了一出包罗社会万象的辛亥年间大戏。他自己对小说结构不太满意,曾经重写。
但这部小说的对话写得极精彩,每一个人物的口吻都很贴切,比如书中黄太太这句:“已经着你惯失得啥子人都不怕了,还叫莫打!”“惯失”就是娇惯的意思,像这样的对白生动活泼,一下子就把人物形象带出来了。再比方说李劼人对人物外貌、行动的描写,讲究而细致,节奏感也好,读得不阻滞。比如《大波》这一段:“他试着把眼一闭。果不其然,一个多玲珑、多妖娆的年轻小跟班,五花大绑绑出辕门,青宁绸镶滚云头边的军衣下面还露出水红里衣;又白又嫩的小脸蛋,已惨变得更其白,白得像石灰;平时多逗人爱的一双极其呼灵的眼睛也呆滞得像死鱼眼睛;柔丝般的头发刷了胶清,在脑顶上挽了个大抓髻,露出羊脂玉似的一段项脖。双膝一点地,那宰把手的钢刀一挥,咔嚓!白嫩可爱的地方,猛然冒出一道鲜红血口,刀锋斫在颈骨上,痛得小跟班啊呀连天地呼娘喊老子。”谁说纯文学难懂,就把这句话砸他脸上。李劼人擅长的,就是把故事写得有生活感。

当代中文创作者喜欢学习新潮叙事技法,在人物、场景描写上却委实差了前辈一截,在这方面,李劼人的描写手法值得学习。
我看《大波》,喜欢有空时随手翻开,兴之所至,读到哪算哪。保路运动距今久矣,我对这本书的情节其实没有那么关心,更感兴趣的是李劼人对社会各阶层、彼时成都城市景观的描绘。譬如噪山雀儿、煞果、幺妹、旋吃旋看这些方言词汇,让小说语言丰富不少。灯影戏、三庆会、保路同志会、汪家拐石花馆、双刀牌纸烟、皇城坝吟啸楼茶铺等物质名词,让我们时隔百年,仍能细致地想象清末民初成都社会的风貌。要了解四川人、四川社会,李劼人的小说堪称最好的向导。只可惜李先生因病去世,这部小说其实并没有写完。

小说中的女人不承担男性的思想
阅读李劼人的读者,很难不为他笔下的女人所动容。
他简直就像是泡在女人堆里,把他见识过的种种女人,大张旗鼓地摆在你面前。小说中的女人不承担男性的思想,也不为任何宏大叙事背书,她们就像现实中我看过的不少川渝人物,有一股生猛的、泼辣的劲儿。她们是不能被控制的,有话直说的,却也是藏着许多小心思的。她们善良、坚韧、讲仁义,在欲望的盐水碱水中翻腾,冲撞了世故,掀翻了禁忌,却也因此头破血流,遭遇世俗的污名。
在1925年—1937年的中国,小说创作的主流是“批判现实”和“浪漫主义”,这其中又以革命文学风头正劲。在民间则是张恨水的小说最流行。在知识分子群体里,对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最为热烈,其代表如蒋光慈及其代表作《少年漂泊者》《咆哮了的土地》,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在当时最被人阅读的一类小说、杂文,也是富有批判现实意味的,像《铸剑》这般的历史传奇则相对小众。在这层背景下,李劼人创作出《死水微澜》无疑开拓了中国小说新的气象。他没有用小说来教化世人,他视语言、叙事为小说的根本,不越俎代庖,让评论家、政治家、新闻人的角色,盖过了小说家的本色。
若说这部小说真有什么倾向,那作者对于妇女无疑是极为同情的,作者有意借邓幺姑、刘三金等角色,反叛和挑战传统中国的礼教,让女性不再是男性文人书写的配角,使她们的生命在被禁锢了两千年的铁屋中有一次真正的浮现。于是,尽管《死水微澜》仍是一部男作家写的小说,但读者看书中女性的心理、女性的活动,却活脱脱像是女人们在站出来说话。
曾有论者将《死水微澜》的女主人公邓幺姑(蔡大嫂)阐释为“中国的包法利夫人”,邓幺姑有一句名言:“人生一辈子,这样狂荡欢喜下子,死了也值得!”她对欲望的态度不是来自于启蒙的教化,而是源于朦胧又强烈的对于自我的感受。她出生乡下,自小不甘平庸,在天回镇,她嫁了个武大郎式的丈夫,当了兴顺杂货铺的掌柜娘娘,可她盼着去成都见市面,她对于男人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,对于旧的乡土与礼教也积聚着一股渴望逃脱的欲望。她先后周旋于袍哥罗歪嘴、顾天成这两个男人,又因念着人情,努力保全蔡兴顺的性命和杂货铺。与其说她是包法利夫人的中国化身,不如说她就是千年来存在的一类女人的文学显现,从潘金莲,到邓幺姑,这样的女性一直存在,她们其实没有变,只是时代的观念变了,影响到书写者的笔墨。

他的人生是一本使人掩卷叹息的长河小说
中国有世情小说的传统,从冯梦龙编选的《三言二拍》,到清末韩邦庆创作的《海上花》,世情小说家喜欢书写城市中的商人、侠客、文人和处在不幸婚姻中的人妇。“大河三部曲”承接了世情小说的传统,又学习了福楼拜、左拉等法国小说家的技巧,堪称现代主义在川渝地区生长出的一轮别致风景。
除“大河三部曲”外,李劼人在1948年写作的《天魔舞》也值得一观。这部小说描绘了抗日战争后期成都社会风貌及世态人情,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和市民心态有很深的揭露。小说于1947年5月6日至1948年3月18日连载于成都《新民报》,共二十九章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整理出版。可惜在影响力上远远不如“大河三部曲”。
2011年,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李劼人全集》,这是迄今对其作品最完整的收录。而早在1955、1956、1958年,人民文学社便先后出版了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《大波》,之后多次再版。读者要阅读他,可以从这两家出版社的版本里进行选择。
关于李劼人的传记,出色者并不算多。我自己心中最好的一本,是龚静染的《李劼人往事 1925——1952》,此书谈李劼人实业救国之路,对其记者、纸厂经营者、厨师、官员等多重身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除这本书外,张义刚的《李劼人评传》也值得作为参考,后者对李劼人有较为“科普”性质的评述。
从青春期时生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学习社会主义等学说,到加入少年中国学会,担任《四川群报》首任主笔,批判地方军阀,再到翻译《包法利夫人》《萨朗波》等法国小说,九一八事变后长期致力于实业救国,李劼人的一生可谓极为精彩,阅读他的作品,最好结合他的人生来看,他的人生就是一本生命能量充沛,又使人掩卷叹息的长河小说。
从诗人穆旦到小说家李劼人,乱世中的那一代文人,实际上有非常强的行动力,他们身兼数职,积极将自我理想付诸实践,他们有骨气、有血性,也有身处岔路口的彷徨。考察那一代知识人,有助于后人对创作与人生、现实与文学的关系,有更为完整的感受。
李劼人最令人可敬的,是他虽然做了许多事,拥有过人的写作天赋,但不喜欢唱高调,洗去了文人常见的自怜自艾,也在慷慨激昂的进步主义奏鸣曲中更关心夹缝中的人。在他的创作中,我们能看到一种认真、谦卑的文学实践,在边地结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果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