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舒心
今年春节伊始,上海芭蕾舞团特别邀约作家茹志鹃的女儿、同为作家的王安忆执笔,为芭蕾舞剧《百合花》担任编剧。母女两代作家隔空“牵手”,成就一段文坛佳话。
“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,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辩证的关系。”王安忆说,沪上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,沸反盈天的,老庄也好,魏晋也罢,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。
她就在这热闹繁华咫尺之遥的所在,安守宁静寂寞。她说,最理想的状态便是“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写”。

1.不是让别人觉得好看,而是自己也有阅读乐趣
上世纪50年代,王安忆出生于文学之家,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,父亲是剧作家、导演王啸平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,热爱文学对王安忆来说并非偶然。
然而,母亲茹志鹃对王安忆不但从来不称赞,反而是挑剔的。在王安忆的印象中,自己小时候很叛逆,很早就脱离母亲的管辖。直到很多年以后,她才知道,自己从母亲那里其实吸收了很多营养。

《百合花》1958年发表在《延河》上
1977年,王安忆写了一篇小说《平原上》,母亲把作品推荐到《河北文艺》上发表,作家贾大山看到王安忆的小说,称赞说,将来她会写出来。他的话对王安忆鼓励很大。
1980年,由《少年文艺》推荐,王安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。半年时间,写下一系列小说,后集册为《雨,沙沙沙》,在《北京文艺》上发表,王安忆自此成名。 1983年,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一同到美国参加国际笔会,回来后发表了《小鲍庄》,成为1985年轰轰烈烈的“寻根”文学思潮的重要收获。
不循规蹈矩,不按部就班,王安忆的创作特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显现出来。她写过包括《流水三十章》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,其写作也和潮流有关:写《小鲍庄》时,她被归到“寻根”文学;写《长恨歌》时,又被归到海派。其实本质上,她一贯保持自我的风格,题材无外乎两类:一类是上海,一类是农村。
那个时代,每个爱写作的年轻人都免不了受到各种创作流派的冲击。王安忆没在弯路上走太远,因为她很快便发现这不适合自己,当然也不妨碍她时不时尝试一下,《众声喧哗》就是小的尝试,脱离了写实主义对小说的规定。《遍地枭雄》《伤心太平洋》是和写实保持距离——没有从头到尾的故事,不是因果式地联系紧密,有潜在的紧张度,整体看来却很涣散。
回顾年轻时的创作,王安忆曾坦言自己“喜欢背叛,不怕失败,很勇敢”。一开始她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,想把前人的规矩破掉,而越往后写,越发现自己的观念越来越合乎、服从前人小说的规定,对故事的要求也越高了。关键不是让别人觉得好看,而是自己也有阅读的乐趣。
2.颠覆容易继承难,需要长时间的积淀
每次见到王安忆,总见她头发挽在脑后,清清爽爽的样子。她不苟言笑,似乎不太容易亲近,可在熟悉她的人眼里,王安忆坦率真实又无比细腻体贴——她亲手织好送给史铁生的毛衣,史铁生去世后,妻子陈希米一直珍存着;作家陈世旭要买藤椅,她跑到家具店亲手一笔笔画下样品(店内不允许拍照)寄给他。30多年前,她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(鲁迅文学院的前身)学习,遇到不会写的字了,转过身问陈世旭,“‘兔崽子’的‘崽’怎么写?”越过几排桌椅,远处的莫伸(作家)插嘴道:“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?”可见她平素在大家眼里的贤淑模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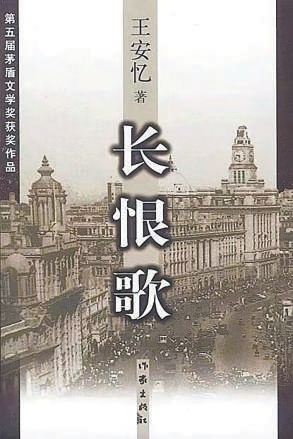
念及王安忆,笔者会想起她在长篇小说《长恨歌》开篇所写:“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……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,它不那么高不可攀,而是平易近人,可亲可爱的。”
《长恨歌》的创作,缘起于一段流言——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,死于非命。 20世纪40年代末期,出身上海弄堂的女中学生王琦瑶偶然地被选为“上海小姐”,由此展开了她充满传奇与变数的人生。开篇以近两万字的篇幅描摹上海的弄堂,并由此延伸开去,将时代的沧桑变幻同个人命运密切关联。小说在对人物内心深度开掘的同时,将上海日常生活中的美感与温情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初写《长恨歌》,王安忆只是被王琦瑶的故事所吸引,没想到发表后,不但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,也成了她所有小说中最具有改编缘的作品,屡屡被拍成影视剧。“写《长恨歌》时,我已经开始注重叙述的趣味性,至少想要这么做。”王安忆透露,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还年轻,也喜欢实验性的写作,“有点儿喜欢炫技,好像怎么样能难倒读者,成了我要完成的任务一样。”
2012年出版的《天香》,却像是王安忆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。书中人生活在明嘉靖年间,离她那么远,而且他们都是自己想象、无中生有的人,这让创作之初的她有些茫然。于是王安忆着眼于人物性格,她相信任何时代人物的性格都不会相差太多。书中虽然没有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中那么多的女性人物,但她们个性鲜明,过眼难忘。《天香》问世后,好评不断,并在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“红楼梦奖”评选中折桂。
如今,王安忆越来越认同,写小说就是讲故事。她很注意情节和审美的取向,若不能在戏剧性上有大的起伏,就要在细节和语言上下功夫。她坦言,年轻的时候,总想颠覆自我,总想要更勇敢的表达,后来才慢慢发现,颠覆容易继承难。前辈积累的东西瞬间便可以颠覆,继承传统却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准备。
写得越多,她也越来越靠近最初写小说的动机——“为什么写小说?就是想听故事。不能说你喜欢听故事,不给别人听。”因此,在《长恨歌》之后,她摒弃了繁复的缺乏故事性的叙事,学会了甄别,学会了放弃,且变得越来越挑剔。“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,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,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,像海绵吸水一样,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。这一时期的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,让它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好、描写也罢,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。”
3.图案在变,针法不变
如果说,年轻时候的王安忆有一种表达的欲望,那么现在,成熟的王安忆在以减法收缩篇幅。
慢的写作追求与生活节奏,让王安忆的日子生出来些许诗意。虽然不喜欢写诗,她的文字却一向充满着清新的意韵。即使是在安徽农村,在和母亲茹志鹃的通信中,既愤怒又渺茫的王安忆,反映自己孤独无助又艰难的生活也是如此动人:“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,但我家的却没有来。”
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,愿意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划清界线。若以此区分,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。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于畅销书优秀元素的吸纳,并且尤其喜欢推理小说。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意大利作家马里奥·普佐、畅销书作家阿瑟·黑利……她觉得,西方小说之所以多伟大的鸿篇巨制,是因为西方小说家发展了坚固、严密而庞大的逻辑推动力,它与宏大的思想互为表里。
莫言看过王安忆的《红豆生南国》之后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:“我看王安忆的小说经常产生联想,仿佛在观察一匹织锦或者丝绸,打开漫长的画卷,上面图案一会儿是牡丹,一会儿是凤凰,图案在变化,具体针法不变……千针万线,一丝不苟,一条跳线都没有。”
某种程度上,这评价可视作王安忆多年来一贯的创作态度。自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《向前进》算起,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已近半个世纪。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作家,她始终如一,以手艺人的勤奋和严谨,一字一句、一砖一石,踏踏实实构建她的小说世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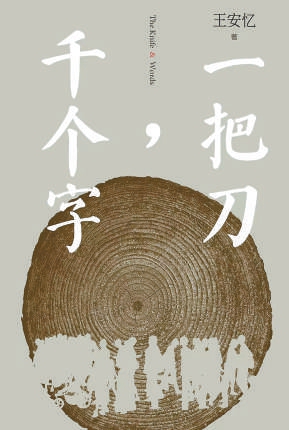
她喜欢手艺人,喜欢听手艺人说话。有一次,王安忆送修家里的一件红木橱具,木器行老板一看便知是民国的物件。她问从哪里看出,对方回答说榫头,接着细数各种嵌榫的方法形制,王安忆听得入了迷。三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里的淮扬厨师,是王安忆在纽约遇见的“原型”,王安忆曾问他各菜系的特色,厨师作答:任何菜系做到最高级便无差别。
王安忆把他写进小说里。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自淮扬名厨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起笔: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,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。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,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,后来在纽约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……故事充满传奇,且讲故事的空间拓展到全球。
王安忆几乎每一部作品,都会从不同的层面给予读者更新鲜更深刻的感受。而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中蕴涵的世道人心和生活哲理,不仅再次证明她情感的饱满与创造力的持久,也成功地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、大历史完美融合。王安忆说,一个写作者,很可能终生都在写一本书,每一本都是未完成,每一本又都是续写和补写。“接”和“续”的是生东西,却是从熟东西里长出来。“所谓‘坚持’,在我可能只是有股子韧劲,还有,思辨对我有吸引力,可能属于理趣的爱好吧。”
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中,主人公陈诚精神世界的启蒙源自《红楼梦》《黄历》《易经》,王安忆的用意是“礼失求诸野”,希望她的主人公以赤子之心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。书中,她还让陈诚游走于各地,从扬州、高邮、哈尔滨,再到旧金山、纽约,以不同地域间舌尖上的美味,开阔出一番融汇了天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。
4.即便虚构,也要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
多年来,王安忆被贴上所谓的“琐碎”标签,并不妥当。准确地说,是“细致”。反映在她的创作中,可以看到王安忆以学者的严谨和认真去完成小说的每个细节。在她看来,即便小说是想象,是虚构,也必须依据现实生活的逻辑。小说的细节尤其需要考据,比如《天香》中的顾绣,《考工记》里的建筑,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中的淮扬菜。对王安忆来说,一旦发现一个好故事并决定写作,必然要研究其发生的背景,写作需要有事实的基础,她希望这基础准确而严格。
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,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。因此,《天香》从嘉靖年间一路写到万历年间,她一路查找资料,给读者最信服的交代。而在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中,选择淮扬菜厨师和王安忆个人经验有关联。从小带她长大的扬州保姆创造了家庭的食风,这一点,王安忆曾在《富萍》中有所表述。小说让舅公带了小孩子穿村走乡办宴,是她得意的一笔,因为只有这地方可以学得厨,又可见得“礼”。而小说涉及的淮扬菜,得到美食家沈嘉禄的赞赏:“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犹如炖生敲,对素材不断地锤炼与升华,便能让读者品读出层次丰富的意蕴。又如小说中屡次提到的煮干丝,此道风味的关键之处在于厨师对豆腐干的前期处理,唯有执爨高手才能‘飘’出银针般的细丝,不粘不团,富有弹性,自成小宇宙。千丝染霜堆细缕,决非一日之功。”
“这部小说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这些人和事都不是我熟悉的,没有心理经验。《长恨歌》写上世纪40年代,有些人在我的成长阶段在街上看到过。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是写我不太熟悉的事情,基本是我经验隔膜的,场域也非常陌生,东北我只去过大连和哈尔滨,淮安也是陌生的,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,倒是对法拉盛的印象还鲜活。我唯一熟悉的是上海。写作强大的动力,是来自思想的动力。”王安忆觉得,由于材料的紧缺,还是有些局促。如果有更丰富的材料,《一把刀,千个字》可以写到三四十万字。
5.文学有时候也像科学,重在发现
“没有作家无所不能。”她坦率地说,写了几十年,仍然还会碰到困难,正因如此,才有写作的欲望。她在克服困难中找到乐趣。如果某一天没有欲望了,那么放弃写作也未尝不可。在描述自己的创作态度时,王安忆说:“写小说时好像体验另外一种人生。坐在桌子前,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:我要把这个人物搞清楚,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——我对这种想象的活动始终没有倦意。”
王安忆喜欢中国一句老话: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。她喜欢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红楼梦》那样的经典之作,也喜欢各种类型小说的推理和悬念,“我当然觉得那些作家高明,我也知道我不是他们。我知道自己的软肋,也没有太大的野心。”王安忆说,她有一些微小的但是个人的目标,就是设定不太遥远的彼岸,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。
王安忆不断在写作中突破自我,《长恨歌》中的语言华丽繁复,这种华丽在《伤心太平洋》达到一种极致,王安忆将其总结为与心境有关。年轻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特别多,来不及涌出来,喜欢堆砌,背后还有一点对事情的表达和把握不够准确。她的语言真正成熟表现在《富萍》,是一种平白的、干净的语言的开始,会斟酌、寻找合适的表达。小说就是从写下第一句开始,进入一种命运。
多年来,王安忆一直保持纯粹而单调的生活和写作。自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授课以来,王安忆先后出版了《心灵世界》《小说课堂》《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——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讲座》《小说六讲》等多部文学讲稿,她在课堂上坦诚分享自己的经验,将所有的文学储备倾囊而出,带领学生探寻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通道,体验阅读与创作的乐趣。“文学有时候也像科学,重在发现。”很多时候,王安忆都在“发现”,在阅读中发现,在写作中发现,在课堂上启发学生发现。
量变到一定程度会达到质变,王安忆在发现中成熟,在发现中进步。虽然人们习惯以“突破”概括王安忆的每一部新书,她本人却更愿意用“进步”形容自己在创作里的努力:“我确实在进步,我对自己的进步是满意的。回过头去看,开始写得也很差,一路慢慢走过来,我的小说逐渐写得比以前好了。”难怪王朔打趣说:“安忆,我们就不明白,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?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,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,你不觉得孤单吗?!”
6.母女跨时空合作,《百合花》绽放舞台

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
今年对王安忆有着特殊的意义,她把母亲茹志鹃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改编成舞剧搬上舞台。
《百合花》最初发表在《延河》杂志上,全篇只有5000多个字,故事也很简单:1946年中秋节,打海岸的部队即将发起总攻。年轻的通讯员接到命令,送文工团女战士前往前沿救护站。救护站里,大家都在为即将打响的战斗做准备,通讯员带着借被子的任务路过新媳妇的家,想问她借那条布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却遭到拒绝。通讯员并不知道那是她新婚的嫁妆,即便文工团女战士从中调解,依然在彼此间留下心结。
一朝分别,再见已是生死永隔,那床还没来得及借出、布满百合花的新棉被,正轻轻覆盖在年轻通讯员身上……茹志鹃巧妙地寓之于小小的百合花,这样的立意,远远超越了口号式宣传的模式。茅盾曾评价这篇小说是“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,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”。
担任芭蕾舞剧的编剧,对王安忆来说,不啻是新挑战。“最难的就是‘借被子’这件小事,太日常、太写实了,怎么搬到舞台上?”为此,2022年10月该创作项目启动后,主创团队就前往小说里故事的发生地——江苏南通海安采风。在母亲曾经战斗、生活过的地方,王安忆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人的革命情怀,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孕育了无数红色基因,留下了一段段动人心魄的记忆,而这正是《百合花》时至今日依然打动人心的原因。
“这么久远的一件作品居然没有被忘记,是很令人欣慰的。”王安忆回忆说,当年母亲的这部小说曾有意改编为电影,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此前的视觉化改编作品,也只有一部早年间不到一小时的学生电影作品,由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沈丹萍饰演“新媳妇”。此次上海芭蕾舞团的舞剧是正式的舞台作品,王安忆参考了当年的电影剧本草稿,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戏剧性扩充,通过美好人性和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比,展现了战争年代别具一格的情愫,让观众感受到战争年代的人性之纯真,之美好。
从小说改编成芭蕾舞剧,那朵曾经打动亿万人的百合花正在今天的观众心中重新绽放。
